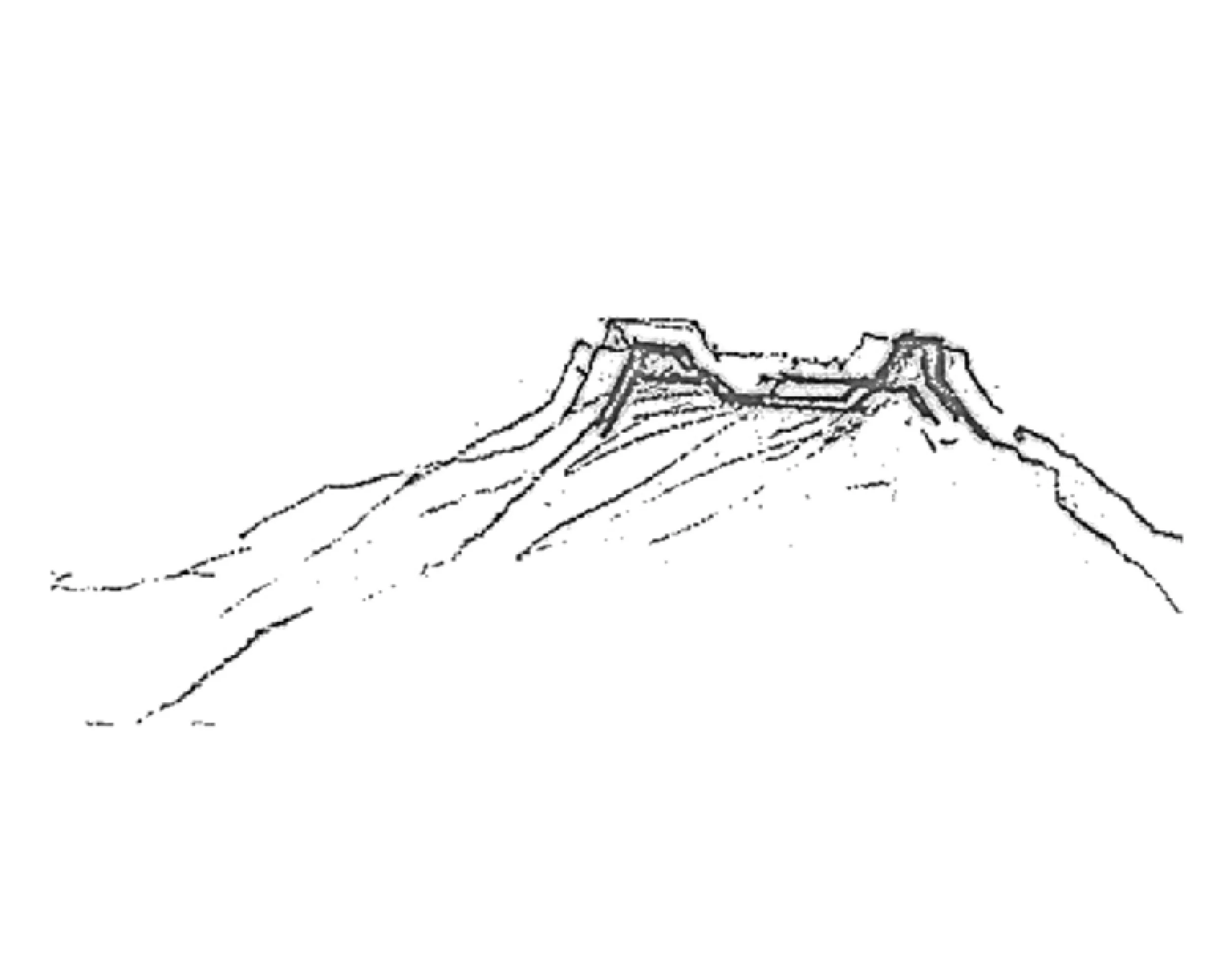寻找地平线——天鹅湖景观廊及观鸟塔
Seeking the Horizon: On the Design of Swan Lake Bridge House and Viewing Tower
建筑与大地
这是一组地景中的建筑。自然而然地,建筑在这里会触及与大地的关系,与风景的关系。
建筑与大地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这是一个带有某种存在意义的追问。正如对人在空间中所处位置的追问:你在空间内部还是外部?还是你同时即在内部又在外部?(图1)建筑与大地的关系,是向上,还是向下?也即建筑从大地上浮升,还是嵌入? 是向内,还是向外?也即建筑是进入大地内部,还是向外部挣脱?
图1 华黎在耶鲁的《空间奥德赛》作业之一:内与外的思考。左图为室内;右图为室外
对这些关系的回应,决定了建筑在场地中作出何样的动作,而这些动作则决定了人对大地的感知,是凌驾于地平面之上,还是被大地所包裹?是伸向外部的无垠,还是静观封闭的内部?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大地对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是脚下坚实的物质?它是重力的来源?是地球母亲的子宫?还是相对于天空的存在?天空对我们又意味着什么,它是头顶无垠的空间?是挣脱后的自由世界?是相对于大地的存在?思考这些基本的问题,却成为意义产生之源。
场地
这是一块面向开阔自然的场地,它的西、南方向面向天鹅湖湿地以及远处的马山。怅然寥阔、水天一色、蒹葭苍苍。这也是一块面向幽深的场地,它的东面是一片长条状的黑松林带,连续、绵延、幽暗,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障。这还是一块刻划进大地的场地,场地中的水面犹如大地的伤口,暴露出大地的肌肤。建筑的任务是在此创造出人可以休憩、观景、摄影、望远的场所。
景观廊
场地周边的地景是浩瀚的、连绵的,既然如此,我无意让它被建筑所阻断。浮升,因此成为建筑第一个重要的意象,也即建筑与地面是脱离的,轻轻地悬浮于地面之上,其下的地表仍然是连续的。这是一个剖面的关系。
一边开阔一边幽深的场地则已经暗藏了一种叙事性,可以产生从逼仄到开放、从阴翳到光明或者相反的变化。我选择将建筑平行紧贴线性黑松林布置,依附于松林使得建筑在场地中的存在感得以减弱,可以保持自然的风景仍是主导。这是一个平面的关系。
基于这样两点最初的意图,建筑的形式自然浮现出来,即是自然中的一道线。由此成形了有71米长的景观廊建筑,在平面上它贴附于后面的松林,剖面上则轻轻地漂浮于地形之上,建筑屋顶的高度低于背景黑松林的轮廓,人工的“线”映衬于自然背景中而显现。而地形从北到南逐渐降低的坡度,加强了对这条线的水平性的感受,以及建筑与地形的逐渐分离所形成的张力。
要实现悬浮,建筑如何支撑于大地上成为关键。支撑点越少、漂浮感越强。由此,桥的形式感开始出现,用尽量少的“墩”来撑起整个建筑,如同一座桥。而墩的数量使其间的跨度成为关键,而要实现较大的跨度,则必须有足够大的梁,这时用墙为梁的想法成为最初的建筑横剖面的来源,纵向的墙体如同工字钢的腹板来承受较大的跨度与悬挑。而沿长向布置的墙的存在在平面上自然形成了一种二元关系:面对松林和面对天鹅湖湿地的空间,即是一种收与放、抑与扬的关系,以此完成在逼仄与开放之间来回转化的空间叙事。
建筑所承载的功能在分段中实现。北段的公共卫生间、中段的庭院与屋顶平台、南段的咖啡厅,这些区域即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而不同的功能使建筑产生出一系列不同的横剖面关系。在北段,从面向城市道路的入口进来,卫生间被两侧的外廊所环绕,面向内部的两个天井采光通风,外廊形成与风景的对话,而阻隔与卫生间之间视线和通风上的联系。在中部,由一个开口上几步台阶进来,挖空的地板形成一段桥,在此可以感受自然地面的连续。过桥则进入建筑最中间一个狭长而封闭的庭院,庭院正对着一部楼梯。当身处庭院中时,外部的风景全部消失了,此时唯有通过顶部长形的开口与天空的接触,而狭窄的楼梯引导人走上屋顶平台,到达屋顶是豁然开朗的一刻,外部的风景以360度全景的方式再次出现,这里成为理想的观景及摄影的场所。在南段,从中心庭院西侧进入室内,经由一道狭窄而只有系列窄条天光所微微照亮的廊道,廊道尽端的光亮将人引向远处的湖景与山景。在廊道的尽端是东西两面完全打开的咖啡厅空间,人在此与风景再次相遇。建筑的最南端从支撑结构悬挑8米,将尽端的咖啡厅空间延伸向远处的风景,人在此与地平线相遇,成为空间序列的高潮。尽端的支撑结构中间是一段向下的楼梯,可以由此下到水面标高来到室外,相当于钻到了建筑的底部。在这里,空间的高度压得很低,可以感受建筑从水面上悬挑伸向前方的张力,而此处的地面低于外部地形的地面,因此这里像嵌进大地内部,经由水上的一段连桥再回到自然当中。
在景观廊中,混凝土材料的使用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基于上述建筑最原始的意图——挣脱重力以实现悬浮与跨越——所对应的结构要求;二是混凝土材料坚实厚重的物质性加强了建筑空间叙事所追求的在逼仄与开放之间转换的体验感。而木纹混凝土一方面赋予建筑感官上的细节以及建造的尺度,另一方面水平铺设的木模板肌理从视觉上强化了建筑水平向的比例感受。
观鸟塔
如果景观廊是关于水平性,那么观鸟塔则是关于垂直性。景观廊是浮升于地表,水平平行于大地,指向地平线,指向无限。而观鸟塔则是垂直于大地,其根部锚固于大地中,上部指向天空,给人提供一种上升的体验。上升的意义在于从不同的高度感受大地。建筑师伍重对墨西哥玛雅人所建造的位于山顶的神庙曾经有过这样的观察:“当玛雅人在丛林顶部的山顶创造这样一个平台时,他们突然获得一个新的生命维度…… 他们在此享有天空、云和微风,突然之间丛林的顶部转化为一个巨大的平原。这一建筑魔术获得一种全新对地景的感受,而且塑造了一种伟大,回应于神的伟大”。 [1](图2,3)
图2 约恩· 伍重草图( 阿尔班山与其上遗址之关系)
图3 奇琴伊察,武士神庙,尤卡坦半岛,墨西哥
观鸟塔内部是一个非常封闭、与风景隔绝的垂直空间,中心通高的柱子加强了这种联系天与地的垂直感,顶部的天光也在强化向上的引导性。经由从外墙木结构上悬挑出来的螺旋楼梯拾级而上,逐渐到达12米的高度,出到室外的观景台,天鹅湖的全景以及地平线尽收眼底,此时方可感受到旁边的黑松林、景观廊建筑的屋顶也连缀成一个平面,一个升起于空中的平面。
与景观廊不同,观鸟塔从结构到外立面都采用了木材。木材的选择是为了让它赋予建筑一种“软”的特性,木材随时间变化的活性,可以消减塔这一高耸之物在环境中过于“硬”的物质性,不让它从自然中过分凸显,甚至营造一种飘摇感,木瓦,与景观廊的木模板相似,赋予塔细节和建造的尺度感。塔的内部则希望木结构能得以清晰地呈现,竖向木龙骨与楼梯台阶结合所形成的韵律感,使得在楼梯上行进时的体验更多是构件所创造的“线”而不是实体的面,可以缓解狭小空间给人带来的促狭感。而在中间的垂直空间中向上看,螺旋楼梯栏板所形成的抽象的面作为背景,强化了对中心柱的感受,这个中心柱并非结构需要,其尺度与比例甚至成为这一空间中的异物,它的意义在于强化对嵌固于大地指向天空的感知。
地平线
在景观廊中,无论在建筑的内部还是屋顶,又或是它的下部,都可以感受到一个水平面的存在,这个水平面悬浮于大地之上,它定义了建筑的边界,或者说人所控制的世界的边界,而它的外部则是广袤的自然。当站在景观廊屋顶的观景平台上时,人可以强烈感受到这个建筑如同一条船,或者一列火车一样,在无垠的自然中向远处的地平线行进。如果说地平线是天空与大地的分界线,那么建筑的边界也如同一个地平线,它是人工世界与自然世界的分界线。意义就产生于建筑形体与地形分离的这一刻,分离赋予了建筑六个立面,包括底部立面;分离细微到建筑地面的楼板与台阶、坡道之间也是脱开的,哪怕只有一两厘米的缝。分离产生了一种建筑的浮游感和不固定于大地的自由感,犹如阿拉丁的魔毯,或者汪洋中的一艘方舟,好像随时可以离去,即便它是由混凝土这样重质的材料所造。
在观鸟塔中,人感受不到外部的地平线,它更像一个联通大地与天空的隧道,又如一个飞船的内部,然而换一个角度看,天窗的边缘也如同地平线,唤起人深处内部对外部世界的感受,好比从飞船的窗户看向太空,只不过它是一个竖起来的地平线。
就此而言,地平线,成为这组建筑所找寻的要素和想要唤醒的一种体验。地平线揭示了天空与大地的关系,人工世界与自然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UTZON Jørn. Platforms and Plateaus: Ideas of A Danish Architect[J]. Zodiac, 1962(10): 113-140.
图片来源:
图1: 华黎
图2: 参考文献[1]
图3: Pomakis. Temple of the Warriors, Chichen Itza [OL].
[2014-09-24]. https://www.ancient.eu/image/3069/.